
摘要:针对近海常见污染物阿特拉津水质基准缺失的问题,本研究搜集了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毒性数据,获得急性毒性数据76个,涵盖10门34科,共38个物种,其中,绿藻门扁藻(Tetraselmis chuii)和褐藻门鼓藻(Bellerochea polymorpha)的种平均急性毒性值为0.02 mg/L,对阿特拉津最为敏感;得到慢性毒性数据32个,涵盖10门18科,共19个物种,其中褐藻门舟形藻(Navicula sp.)的种平均慢性毒性值为0.004 3 mg/L,对阿特拉津最敏感。基于收集的急、慢性毒性数据,利用物种敏感度分布(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 SSD)法推导出阿特拉津的短期和长期水质基准分别为6 600和1 975 ng/L。此外,本研究中还发现莱州湾海域表层海水中阿特拉津的检出率为100%,浓度范围为48.15~118.24 ng/L。风险商法和联合概率曲线法均显示莱州湾海水中阿特拉津的生态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这些结果可为制订阿特拉津的海水水质标准、评估其生态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阿特拉津,作为一种三嗪类除草剂,因其低成本和出色的除草效果,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1]。2018年,阿特拉津的全球销售额高达6.55亿美元,占三嗪类除草剂市场份额的46.8%[2],在中国农业上的年使用量约为1 000~1 500 t[3]。尽管其效果显著,但阿特拉津在土壤中的半衰期较长,约为150~360 d, 这意味着它有可能长期存在并污染我们的环境。更糟糕的是,这种化学物质在施用后会进入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最终汇入海洋,成为海洋环境中的常见污染物[4]。在中国海州湾和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水中,阿特拉津的浓度分别达到了61.9和730 ng/L[5-6]。另外,在中国海参样品中也检测到了阿特拉津,含量为0.9~3.62 μg/kg[7]。
随着阿特拉津在海洋环境与生物体内不断被检出,它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这种化学物质不仅对海洋生物产生直接毒性效应,而且通过食物链累积,对更高营养级的生物产生影响。例如:将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暴露于3.2 μg/L阿特拉津7 d后,其叶绿素a含量显著降低,细胞结构受到破坏,种群生长受到抑制[8];Bejarano等[9]发现,将3种常见桡足类(Enhydrosoma baruchi,Onychocamptussp.和Paronychocamptus wilsoni)暴露于26 μg/L阿特拉津28 d后,其丰度明显降低,进而改变了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另有研究报道,将大西洋鲑鱼(Salmo salar)暴露于100 μg/L阿特拉津10 d后,出现了离子调节、生长和内分泌紊乱的情况[10]。鉴于阿特拉津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制定相应的海水水质基准(Water quality criteria, WQC)显得尤为重要。WQC指水环境中的污染物或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或水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影响的最大浓度[11]。WQC的推导方法有评估因子法(Assessment factor, AF)、物种敏感度排序法(Species sensitivity rank, SSR)和物种敏感度分布法(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 SSD)等[12]。Chen等[13]利用AF法,将绿藻的半数效应浓度(Median effect concentration, EC50)除以100,得到阿特拉津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 PNEC)为1 050 ng/L;Papadakis等[14]同样利用AF法将藻类的无观察效应浓度(No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 NOEC)除以10,得到阿特拉津的PNEC为10 000 ng/L。Caquet等[15]使用SSD法拟合阿特拉津对藻类的NOEC值,推导出5%物种危害浓度 (Hazardous concentration for 5% of the species, HC5)值为2 200 ng/L。以上这些研究中所用的生物毒性数据较少,且主要基于单一生物类群的数据,难以为制订阿特拉津的海水WQC提供有力支撑。
为制定阿特拉津的海水WQC提供有力支撑,本研究搜集和筛选了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利用SSD法推导了阿特拉津的长期和短期海水WQC。同时,还调查了莱州湾海水中阿特拉津的污染现状,并利用本研究推导的长期海水WQC评估了阿特拉津在该海域中的生态风险。
1、材料与方法
1.1 阿特拉津
阿特拉津,化学名称为2-氯-4-乙胺基-6-异丙胺基-1,3,5-三嗪,分子式为C8H14ClN5。其在海水中的半衰期约为27.7 d, 主要降解产物为去乙基阿特拉津与去异丙基阿特拉津[16]。
1.2 毒性数据的搜集与筛选
本研究从美国环保署(US EPA)的生态毒理数据库、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搜集已发表的阿特拉津毒性数据,时间截至2022年1月1日。根据《HJ 1260—2022 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技术指南(试行)》[11]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水质基准制定的指导方针”[17]对数据进行筛选。对于急性毒性数据,暴露时间以1~4 d为宜;对于慢性毒性数据,微藻的暴露时间应大于1 d, 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的暴露时间应不少于7 d, 大型无脊椎动物的暴露时间不少于14 d, 鱼类和两栖类的幼体和成体的暴露时间应分别不少于7和21 d。搜集的毒性数据应至少涵盖3个营养级,至少包括10个物种,且涵盖以下生物类群:1种鱼科、2种甲壳科、1种非鱼类的底栖动物、1种浮游植物和1种水生维管束植物。当同一物种存在多个毒性数据时,取其几何平均值作为该物种最终的种平均急性和慢性毒性值。
1.3 水质基准推导
利用搜集的毒性数据,以物种的毒性数据为x轴,以物种毒性数据的累积概率为y轴,构建SSD曲线。通过计算得到HC5值,再将HC5除以一个评估因子(取2)得到水质基准[18]。使用正态分布(Normal)、对数正态分布(Log-Normal)、对数逻辑斯蒂分布(Log-Logistic)和Bull Ⅲ分布等常用模型进行数据拟合。采用基于R语言的SSD Tools软件进行数据的拟合。
1.4 莱州湾海水样品采集
如图1和表1所示,选取莱州湾作为调查海域,共设置了14个站位,于2021年3月进行采样。使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取表层(水深50 m以上)海水,通过GF/F玻璃微纤维滤膜(孔径0.22 μm, 直径47 mm)进行过滤后运回实验室,以用于阿特拉津的提取。
图1 莱州湾取样站位
表1莱州湾各站位坐标以及阿特拉津浓度
1.5 阿特拉津的测定
将400 mL过滤后的表层海水与10 μL同位素内标母液(阿特拉津D5,100 μg/L)混匀后,利用预先活化的固相萃取柱(Oasis HLB)进行抽滤富集,用5 mL甲醇进行洗脱,将洗脱液收集在玻璃管中。然后将玻璃管中的洗脱液进行氮吹干燥,用复溶液(乙腈∶水=1∶9)进行复溶后,利用1 mL注射器将复溶液移出并过滤至色谱瓶中。根据Mazzella等[19]的方法,使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HPLC-ESI-MS/MS)对阿特拉津进行测定。为验证方法的可靠性,设置了3个空白水样进行潜在污染分析,均未检测出阿特拉津。在固相萃取之前加入标准品测定回收率,监测样品预处理与仪器分析过程中的误差。本研究中阿特拉津的检出限为3 ng/L,回收率为96%,相对标准偏差为12%。
1.6 生态风险评估
1.6.1 商值法
商值法的公式为
RHQ=AEC/BWQC。
式中:RHQ代表阿特拉津环境浓度与水质基准的比值;AEC代表阿特拉津在环境中的浓度;BWQC代表水质基准。根据RHQ的大小可以将风险水平分为四级:RHQ<0.1表明阿特拉津的生态风险可以接受;0.1≤RHQ<1表明存在低风险;1≤RHQ<10表明存在中等风险;RHQ≥10表明存在高度风险[20-21]。
1.6.2 联合概率曲线(JPC)法
本文使用风险评估软件BMC-SSD构建联合概率曲线(Joint probability curve, JPC)[22-24]。JPC是在得到毒性数据SSD曲线和阿特拉津环境浓度累积频率分布的基础上,以毒性数据SSD曲线的纵坐标为JPC的横轴,以超过毒性数值的环境浓度百分比为纵轴,形成累积剖面图,JPC与坐标轴之间的面积即为预期的生态风险[25]。
2、结果
2.1 阿特拉津的毒性数据
本研究共搜集到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数据76个,涵盖10门34科,共38个物种,如表2所示。急性毒性数据从0.020 mg/L (扁藻(Tetraselmischuii)和鼓藻(Bellerochea polymorpha), EC50)到1 000 000 mg/L(扇蟹(Neopanopetexana), LC50) 不等。最敏感的物种与最不敏感的物种相差很大(相差约50 000倍)。在种平均急性毒性数据中,藻类和甲壳类数据最多,分别占比为44.7%和39.5%。
本研究共搜集到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慢性毒性数据32个,涵盖10门18科,共19个物种,如表3所示。慢性毒性数据从0.004 mg/L(舟形藻(Naviculasp.), LOEC)到30.000 mg/L (月光螺(Marisa cornuarietis), NOEC) 不等。最敏感的物种与最不敏感的物种相差约6 900倍。在种平均慢性毒性数据中,藻类、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数据最多,分别占比为52.6%、15.8%和15.8%。
表2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数据
表3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慢性毒性数据
2.2 模型拟合与水质基准的推导
使用5种模型对阿特拉津的急性和慢性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表明 Anderson-Darling(AD)和Kolmogorov-Smirnov(KS)检验均为P>0.05。AIC和AICC检验结果接近,其中Log-Gumbel模型的AICC值最小,参数Delta为0,如表4所示。因此,本研究选择Log-Gumbel模型对阿特拉津的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拟合SSD曲线,得到HC5值分别为13 200 ng/L (见图2)和3 950 ng/L (见图3)。通过HC5值除以评估因子,得到阿特拉津的短期和长期海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分别为6 600和1 975 ng/L。
表4阿特拉津海水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的五种拟合模型相关参数
图2 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数据SSD拟合曲线
图3 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慢性毒性数据SSD拟合曲线
2.3 莱州湾海域阿特拉津的空间分布
在莱州湾海域的14个站位的表层海水中,阿特拉津的检出率为100%,浓度从48.15 ng/L到118.24 ng/L不等(见表1)。从整体上看,阿特拉津的浓度呈现出由南部沿岸向北部海域递减的趋势(见图4),其中,站位B8和B6的阿特拉津浓度最高,分别为118.24和104.71 ng/L,站位B8的阿特拉津浓度分别是站位B3和B4的2.46和1.81倍。
2.4 生态风险评估
基于本文推导的长期海水水质基准(1 975 ng/L),对阿特拉津浓度最高的站位B8进行风险评估,通过商值法得到RHQ为0.06(< 0.1)。结合莱州湾14个站位检测到的阿特拉津浓度,使用BMC-SSD软件导出联合概率曲线。如图5所示,阿特拉津在莱州湾表层海水中的总体风险概率中值和均值分别为1.04%和0.79%。
图4 阿特拉津在莱州湾的空间分布
图5 莱州湾表层海水中阿特拉津的联合概率曲线
3、讨论
本研究共获得阿特拉津对38种海洋生物的平均急性毒性数据,发现绿藻门扁藻(Tetraselmis chuii)和褐藻门鼓藻(Bellerochea polymorpha)对阿特拉津最为敏感,平均急性毒性值为0.02 mg/L。相比之下,节肢动物门的扇蟹(Neopanope texana)对阿特拉津最不敏感,平均急性毒性值达到1 000 mg/L。同时,慢性毒性数据显示褐藻门舟形藻(Naviculasp.)对阿特拉津最敏感,而软体动物门的月光螺(Marisa cornuarietis)则最不敏感。有研究表明,具膜舟形藻(Navicula pelliculosa)对与阿特拉津同为三嗪类除草剂的扑草净非常敏感,慢性毒性值仅为300 ng/L[63],这与本文得到的舟形藻对阿特拉津慢性毒性最敏感的结果一致。阿特拉津主要通过破坏植物光合系统Ⅱ (PS Ⅱ)反应中心来抑制受体和供体的电子传递[64]。浮游植物作为海洋初级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固碳合成糖类、脂质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构成了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食物网初级生产力的基础[34]。在本研究中发现,浮游植物对阿特拉津最为敏感,因此特别提示应关注三嗪类除草剂对海洋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SSD法是中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规定使用的水质基准推导方法。本研究利用5种模型拟合了阿特拉津的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其中Log-Gumbel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最好,这与秦璐等[65]使用SSD法拟合除草剂高效氟吡甲禾灵的毒性数据时优选的模型一致。本研究推导阿特拉津的长期海水水质基准为1 975 ng/L,与加拿大保护水生生物的阿特拉津水质基准和欧盟规定的阿特拉津最大容许浓度(分别为1.8和2.0 μg/L)相近[5]。Moore等[66]使用SSD法拟合阿特拉津对水生自养生物的EC50值,推导出阿特拉津的HC5值为28.4 μg/L,明显高于本研究推导的水质基准。这可能是因为前者没有区分海水与淡水生物。考虑到盐度会对污染物的毒性具有明显影响,在推导海水水质基准时应该选择海洋生物毒性数据[17]。有研究表明,1 μg/L阿特拉津对大叶藻(Zostera marinaL.)、丛生大叶藻(Z.caespitosaM.)和红须根虾形藻(Phyllospadix iwatensisM.)的光合作用未产生显著影响,而暴露浓度达到5 μg/L时,对3种海草的光合作用抑制率为6.89%~8.94%[67]。另有研究表明,将海葵(Exaiptasia diaphana)暴露于3 μg/L阿特拉津2周后,而其谷氨酸水平得到显著上调[68]。此外,本研究搜集到的阿特拉津对海洋生物的最低观察效应浓度(Lowest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 LOEC)均高于推导的阿特拉津海水水质基准。可见,本研究推导的阿特拉津海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有效保护,因而可为制订海洋中阿特拉津的WQC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中,阿特拉津在莱州湾海域的浓度范围为48.15~118.24 ng/L,这与徐英江等[69]报道的浓度(6.82~83 ng/L)接近。对中国大连海域和澳大利亚大堡礁海域的多项研究发现,除草剂在近岸浓度较高,特别是河口区的阿特拉津浓度可达到0.4~3 μg/L[5,70]。在本次阿特拉津调查中,莱州湾南部的B8站位浓度最高(118.24 ng/L),这可能是由莱州湾南部有较多河流汇入莱州湾海域所致,如胶莱河、潍河、白浪河和小清河等,这些河流沿岸是重要的农业区,可能存在较高的阿特拉津残留。2种风险评估结果都表明,莱州湾海域的阿特拉津尚未造成明显的影响,风险可以忽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莱州湾有多条河流汇入,这些河流可能携带阿特拉津。在复杂的近海河口环境中,阿特拉津浓度受季节影响较大,因此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一步调查阿特拉津的污染状况。
4、结论
(1)阿特拉津的短期和长期海水水质基准分别为6 600和1 975 ng/L。
(2)阿特拉津在莱州湾表层海水中的浓度范围为48.15~118.24 ng/L,并且在南部河口沿岸海域污染水平最高。
(3)莱州湾海水中阿特拉津的生态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但仍需要关注汛期入海河流排放对阿特拉津污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北南,宋晓,贺琳娟,等.莠去津和芴对斑马鱼胚胎的联合毒性效应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21,40(10):2086-2094.
[2]顾林玲.三嗪类除草剂研究与开发新进展[J].世界农药,2021,43(12):12-23.
[3]刘勇攀,张衿潇,蒋燕虹,等.功能化材料Zr@AC对水中难降解农药阿特拉津的去除特征[J].环境科学研究,2022,35(3):750-760.
[6]张望,范广宇,孟祥龙,等.海州湾沿岸海水中21种除草剂的分布特征[J].江苏农业科学,2019,47(23):289-294.
[7]张华威,刘慧慧,田秀慧,等.凝胶色谱-固相萃取-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产品中9种三嗪类除草剂[J].质谱学报,2015,36(2):177-184.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HJ 1260—2022 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技术指南(试行)[S].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2022.
[12]解瑞丽,周启星.国外水质基准方法体系研究与展望[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2,34(6):939-944.
[63]郑磊,杨文龙,董亮,等.扑草净水环境质量基准及风险评估[J].中国环境科学,2021,41(8):3825-3831.
[65]秦璐,宋秀凯,刘丽娟,等.高效氟吡甲禾灵对海洋生物的急性毒性与水质基准推导[J].环境科学研究,2022,35(6):1509-1518.
[67]高亚平,蒋增杰,杜美荣,等.除草剂扑草净和阿特拉津对海草与大型藻类的毒性比较[J].水生生物学报,2017,41(4):930-934.
[69]徐英江,刘慧慧,任传博,等.莱州湾海域表层海水中三嗪类除草剂的分布特征[J].渔业科学进展,2014,35(3):34-39.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18YFC14076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964025)资助~~;
文章来源:王辉,隋傅,高晨,等.阿特拉津海水水质基准及在莱州湾的生态风险评估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4(09):78-87.
分享:

抗生素是一类由微生物产生或化学合成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医学、农业生产、水产以及畜牧养殖[1]。据报道,全球每年抗生素使用量为10万吨~20万吨,并逐年上升[2]。我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医疗业和畜牧养殖业抗生素滥用问题相对严重。
2024-11-19
邻苯二甲酸酯主要以物理方式添加于塑料中,因此,在其制造、应用和废物处理过程中极易释放到环境当中[2]。不可避免地,人类会通过饮食摄入、空气吸入和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于PAEs[3],进而引发生殖、心血管和代谢系统紊乱异常等健康风险[4-5]。
2024-11-19
近海是水圈、生物圈和大气圈等圈层的典型交汇区域,区域内各类活动剧烈、物质交换频繁[1]。全球三分之二的特大城市位于近海地区[2],使得近海海域接纳了大量人类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其中包括以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为代表的芳香族有机化合物(aromatic organic compounds,AOCs)。
2024-11-19
加强环境监测和数据收集,建立科学的环境评估体系,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总体改善,沿海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海洋环境监测是准确、及时和全面掌握海洋环境各要素时空分布、变化及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是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的重要支撑。
2024-11-14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海上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快速发展,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省份,其海上风电项目也在近年来得到了积极推动和建设。福建拥有长达3 000多千米的海岸线,海岸线长,风力资源丰富,适宜海上风电的发展。
2024-11-11
有研究报道,将大西洋鲑鱼(Salmo salar)暴露于100 μg/L阿特拉津10 d后,出现了离子调节、生长和内分泌紊乱的情况[10]。鉴于阿特拉津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制定相应的海水水质基准(Water quality criteria, WQC)显得尤为重要。WQC指水环境中的污染物或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或水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影响的最大浓度[11]。
2024-08-27
近海岸生态系统在维护海洋环境、调节气候及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保护并及时修复受损的海岸生态系统意义重大。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草本植物具有种间竞争力强和繁殖速度快等特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是一种沿海滩涂入侵物种,部分近海岸因互花米草生物入侵而使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2024-08-0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是我国新时代“人地关系”发展的前沿问题之一。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洋经济和海岛经济加速发展,资源环境因素对海岛旅游开发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全国海岛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实施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探索建立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海岛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为新时代海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指明了方向。
2020-12-14
海水营养盐是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生物生存和繁殖的物质基础。它参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整个过程,因此其含量与分布直接影响浮游植物的生长,甚至改变群落结构。珊瑚礁生态系统是一个高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的特殊海洋生态系统,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极好的自然条件。
2020-12-07
冯家江流域是北海国家级滨海湿地公园的“生命线”,其水质和泄洪能力直接影响下游的岸滩稳定和红树林生长注:单因子评价结果大于1的以加粗标出。环境。本文根据2016年6月和2019年6月两次在冯家江入海口邻近海域进行的水质调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以期了解该海域水质变化情况并探讨可能的原因。
2020-10-27
人气:5317

人气:4947

人气:4937

人气:4621

人气:3362
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海洋环境科学
期刊人气:1094
主管单位:国家海洋局
主办单位: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海洋环境科学学会
出版地方:辽宁
专业分类:环境
国际刊号:1007-6336
国内刊号:21-1168/X
创刊时间:1982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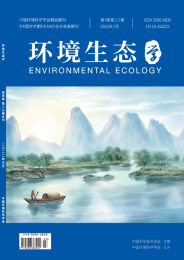
影响因子:1.587

影响因子:0.566

影响因子:1.350

影响因子:0.000

影响因子:0.932
400-069-1609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